長崎的信仰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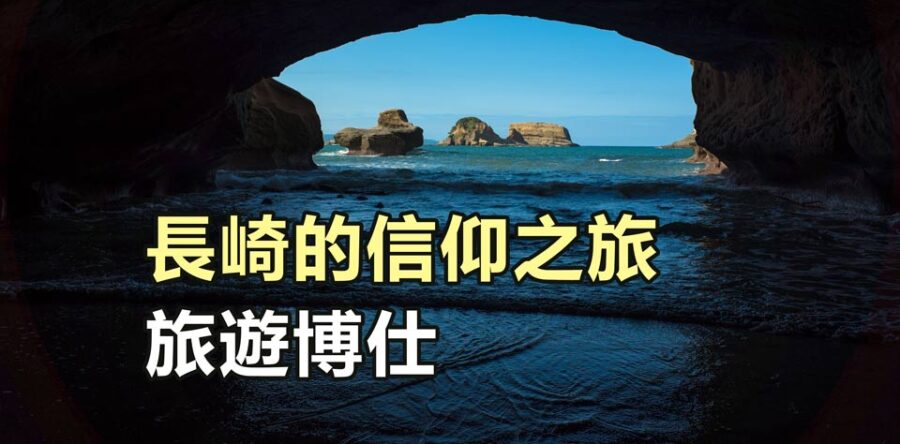
日本向來被形容為福音硬土,在這片硬土上,曾經發生過無數可歌可泣的殉教故事。16世紀,從歐洲而來的宣教先鋒們在這片土地上灑下他們的烈血。這趟我專程前往長崎的探索之旅,希望可以踏著前人的足跡,尋找宣教士留下的佳美足跡。這可以是歷史的追尋,也可以是心靈的覺醒。無論是走在大浦天主堂前的石坂,或是走進平戶第一座天主堂,每一步都將揭開一段埋藏的記憶,與一段無聲的信仰史。當我決定踏上長崎的土地時,心中並未懷抱宏大的目的,只是被一種無形的力量牽引。
「惡人吞滅比自己公義的,你為何靜默不語呢?」(哈巴谷書一章13節)
人在苦難中的沉重與無力,而上帝好像默不作聲。

人們所認識的長崎,是因為一顆原子彈。1945年8月9日上午11時02分,一顆名為Fat Man的原子彈從天而降,吞噬了整座城市。事實上,長崎作為原爆目標似乎是一個倉促的決定;原來轟炸的目標是九州的小倉,但當轟炸任務的飛機抵達小倉上空時,卻發現小倉被雲霧籠罩,根本無法通過目視來確認投彈目標。當時轟炸機隊被要求一定要看到目標才能確保有效轟炸。因此,他們在最後一刻放棄轟炸小倉,轉向次要目標:長崎。直到今日,日本人還會用「小倉的運氣」來形容命運的安排。
浦上天主堂瞬間化為平地,頹垣敗瓦中只剩下一些殘缺的石像,彷彿看見他們的無奈。。四百多年的信仰與四萬具肉體同時在五千度高溫中蒸發。但又有多少人會知道,在這場災難之前,這座城市曾經燃燒過信仰的火焰?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將公理傳開。他不灰心,也不喪膽,直到他在地上設立公理;海島都等候他的訓誨。

我站在酒店的露台上,凝望著對岸,那片曾經見證奇蹟與風暴的海洋。四百多年前,平戶港的浪花中,不只有商船的桅杆與異國香料的氣味,更承載著一種無形的重量:十字架的微光,正隨葡萄牙帆船悄悄泊岸。

這個港口曾經是東西相遇的門扉,商人們追求黃金,傳教士追尋靈魂;鐵砲與聖經,在此交織成一段矛盾的歷史。當第一座教堂在長崎最南端的種子島矗立起來,這裡的土壤接納了基督,也埋下了信仰的種子。然而,歷史的浪潮從不寧靜,恩典與迫害、接納與背叛,如同潮汐反覆沖刷著這片土地。

那些未被浪花抹去的痕跡,潛藏於漁村民謠中的拉丁禱詞、老工匠木雕中隱晦的十字紋,它們都是沉默的證人,訴說著一群人在黑暗中緊握光明的故事。
讓我們以「恩典」為舟,逆流回溯這段被遺忘的航行,當信仰穿越宗教與文化的暴風,如何在人的心中錨定永恆?
1543年,一艘載著葡萄牙商人的中國帆船因風暴漂流至日本九州南端的種子島,開啟了日本與歐洲接觸的「南蠻貿易」時代。短短六年後,1549年,耶穌會傳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踏足鹿兒島,正式將基督教傳入日本。然而,真正讓基督教在九州扎根的地區,卻是平戶港,一個位於長崎縣西北部的天然良港,因地利之便,成為16世紀東亞貿易網絡的核心樞紐。

1550年,葡萄牙商船首次駛入平戶港。當時的平戶藩主松浦隆信(まつら たかのぶ)敏銳意識到,與「南蠻人」貿易能帶來巨大的經濟與軍事利益。葡萄牙人帶來的火槍及鐵砲,革新了日本戰國時代的戰爭模式,而歐洲商品的轉口貿易更讓平戶繁榮一時。為了鞏固貿易關係,松浦對傳教士的活動採取包容政策。1562年,耶穌會在平戶建立日本第二座教堂(聖方濟沙勿略紀念教堂),(IMG_9086),並以此為據點向周邊地區傳教。傳教士們深諳「自上而下」的傳教策略,他們向松浦氏贈送西洋鐘錶、眼鏡等珍奇物品,並透過醫療與教育服務贏得民眾信任。
至1570年代,平戶已有數千名基督徒,甚至出現日本最早的基督徒武士團體。然而,宗教寬容的背後暗藏危機。隨著基督徒勢力擴大,佛教寺院與神道教勢力開始不滿。更關鍵的是,豐臣秀吉於1587年頒布《伴天連追放令》,禁止傳教士活動。儘管平戶因貿易價值暫免於迫害,但松浦氏的政治搖擺已預示風暴將至。





